- 时间: 1632729799323
- 来源: 侨报网综合
【侨报网综合讯】北京时间27日早6时,中国翻译家、德语文学专家叶廷芳在北京因病去逝,享年85岁。他去世的消息传出后,中国文学界多位名人纷纷表达了对这位“中国翻译卡夫卡第一人”的怀念。
文坛缅怀:他翻译的卡夫卡影响了无数人
据上海《文汇报》、广州《羊城晚报》、成都红星新闻等多家媒体报道,叶廷芳去世后,中国社科院外文所、中国作协均发布了相关消息。大陆文学、出版及其他各界人士也纷纷悼念追思。
中山大学教授、资深文学理论家谢有顺在微信朋友圈写道:“缅怀!哀悼!恐怕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译者了。读卡夫卡,完全重塑了我的文学观。仅见过叶先生一次,说了不到五句话,表达的全是敬佩之情。”
诗人于坚表达了深切的怀念:“二十多年前我旅京时,与先生过从较密。他是一位真人。我记得我们在黑暗里穿过团结湖附近的街边花园,没有谈到卡夫卡,我们谈到人生,两性关系和一些好玩的事。丑陋的建筑物被黄昏之光照得很美,他的那只空袖子在晚风里飘。怀念长者。”
作家阿乙还记得,当年读了叶廷芳先生编选的《卡夫卡短篇小说全选》,带着这套书去了常居的所有城市。“正是叶廷芳先生翻译的卡夫卡,使我从一名文学青年变成作者。他让我忘记等级森严的殿堂,鲁莽而富于激情地去写,仅仅去写。他对我起的作用就是解放。”
独臂译者:最早把卡夫卡介绍到中国
叶廷芳于1936年11月23日出生在浙江衢县(现为衢州市衢江区),9岁时不慎跌伤,失去了左臂,并因残疾几度失学,后历经波折考上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专业,师从冯至。1961年毕业后留任助教。

1964年,他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,历任外国文学研究所《世界文学》杂志编辑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中北欧文学室主任、研究员。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叶廷芳是第九届、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,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会长,中国环境艺术学会理事,中国残联评委会副主任,中国肢残人协会副主席。
叶廷芳被视为大陆学界翻译卡夫卡作品的“第一人”。他最早把欧洲文学大师卡夫卡介绍到了中国,1990年代主持编译了《卡夫卡全集》,先后翻译过卡夫卡的小说、随笔、日记和书信,译有《迪伦马特喜剧选》《老妇还乡》《卡夫卡文学书简》《卡夫卡信日记选》《卡夫卡随笔集》等。
此外,他对现代主义、布莱希特、迪伦马特这些名字如数家珍,撰有大量有关建筑、戏剧、美术等方面的评论和散文随笔,著有《现代艺术的探险者》《卡夫卡,现代文学之父》《现代审美意识的觉醒》《掉入世界的陌生者》《西绪弗斯的现代原型》《论悖谬》《西方现代文艺中的巴罗克基因》《德语国家短篇小说选》《德国书话》《外国名家随笔金库》《外国百篇经典散文》《外国文学名著速览》等30余部作品。
翻译“无法无天” 精准之外追求“传神”
成都封面新闻报道,叶廷芳曾说,“如果没有断臂之痛,我很可能就是浙江衢州的一个农民或基层干部;如果不经历不同于常人的生命体验,我就不会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坚毅品格。”他给自己立下人生军令状——超越正常人,而他也确实做到了。

在翻译方面,叶廷芳认为,文学翻译是所有翻译中难度最大的一种,因为文学作品不是科学的产物,而是人类心灵与缪斯结缘的一种审美游戏。它常常不守规矩,无法无天,擅自越出语言和语法的疆界,也找不到一把标准的尺度来衡量。因此,它对译者的文学修养、语言表达、审美创造等综合素养是一种考验。
叶廷芳认为,严复提出的“信、达、雅”这三种境界很难兼得,如果原作本身很“雅”,翻译的时候也应尽可能“雅”;如果原作很通俗,或者很泼辣,你也翻译得很“雅”,那就跟“信”相冲突了。“信、达”是翻译家的职守,“传神”才是翻译追求的目标。要拿捏好翻译的尺度和分寸,首先必须尊重原作的语言特点和风格。(完)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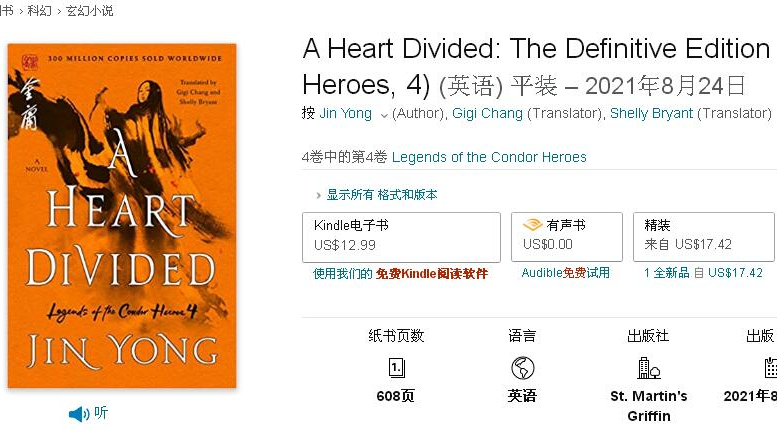

继续加载...